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解释
- 欧洲杯直播
- 2024-12-24 22:19:17
- 13
【摘要】金融衍生交易特别是场外衍生交易规则与传统民商法之间的冲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衍生工具作为一种新的合同类型,与传统合同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前订约、未来履行”,从中派生出特殊的履约风险、缔约风险等一系列新问题。对赌、显失公平等法律争议正是基于衍生合约本身的特性而产生;而通常被称为“衍生交易规则”的一整套制度实际上是市场自发创设的防范履约风险的安排。在此,场外衍生交易与场内衍生交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需要应对同样的问题。通过还原衍生交易规则背后的法律逻辑,可以构筑一个以“合同”为中心的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容纳从合同效力、履行、缔约到信息披露、监管等一系列问题。以合同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民商法应扩张自身的体系以容纳实践中产生的新合同类型,从而为整个金融衍生交易法律规则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衍生交易;衍生交易规则;民商法;合同 引言:问题的提出
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交易[1]在过去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由此也导致这种新型交易形态与传统法律制度特别是民商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金融衍生交易被公认为现代经济生活中最为复杂的商事交易形态,其精巧的交易结构、复杂的交易关系已经令非金融专业人士望而却步,而从市场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套特殊的交易规则与传统民商法理念之间的差异,更增加了法律人理解金融衍生交易的障碍。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围绕着制定期货交易司法解释的争议,充分体现了场内衍生交易规则对传统观念的冲击。[2]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与境外投行之间的金融衍生交易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以及以KODA血洗大陆富豪事件为代表的个人结构性理财产品纠纷,又将场外衍生交易推到国人面前,[3]对司法机关、政府监管部门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某些结构性理财产品案件中,金融机构与客户、法律人士的观点截然对立,监管者与法院之间则相互推诿,有些纠纷甚至陷入“消费者维权,监管者建议走司法程序,法院因看不懂产品说明书而未予受理”的怪圈。[4]更多的时候,法院虽然受理了案件,但苦于裁判无以为据,或者对当事人提供的所谓“国际惯例”--由国际互换及衍生交易协会(ISDA)主持制订并广泛适用于全球场外衍生交易的主协议文本(以下简称ISDA主协议)--难以裁断。[5]
目前,我国有关金融衍生交易特别是针对场外衍生交易的专门立法几乎是空白,[6]而以ISDA主协议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交易惯例对国人来说也很陌生,更何况这些惯例源于纽约、伦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浓厚的普通法色彩俨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法律观念相左。尽管近年来我国金融实务部门强烈呼吁承认金融衍生交易特别是场外金融衍生交易的特殊性,[7]甚至出台了中国版的ISDA主协议--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以下简称NAFMII主协议),但在立法未予回应之前,即使是奉行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官也未必敢在缺乏法理支持的情形下贸然裁决。然而,当前学理上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研究却多集中于金融衍生交易的监管或规制问题,鲜少关注交易层面的法律冲突。即使是为数不多的针对微观问题的讨论,也常常套用金融或商业术语,如衍生交易的法律特征包括“虚拟性”、“杠杆性”、“高风险性”;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醉心于某种高深玄妙的描述,如“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的出现一方面模糊了传统物权和债权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使传统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类别的划分出现了矛盾”等等。[8]
当然,金融衍生交易对法律人提出的挑战并非我国独有。从域外来看,2008年以来,德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地区也相继出现围绕着金融衍生交易法律适用的重大争议。当地法官基于传统民商法理念作出的判决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9]即使是在金融衍生交易最为发达的英美国家,针对衍生交易的司法实践也并不令人满意。美国著名的衍生交易法律专家帕特诺伊(Partroy)教授指出:“普通法在这个领域中的规则严重匮乏。解决纠纷的代价非常昂贵,很少有公开的判决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指南。即使是案件事实都很难从判决书中得到确认,当事人的诉求通常未能准确地描述其所争议的衍生交易,遑论最终的司法意见。……法官尽可能避免触及争议的核心问题,或者是害怕其创设的先例对市场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者是被争议的细节和复杂程度给吓退了。”[10]
其实,无论是将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神秘化还是对此感到绝望或排斥,都不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实际上,法律人对于理解金融衍生交易有着天然的优势。金融衍生交易作为商事交易,是建立在合同、担保等一系列民商事法律制度基础上的现象,甚至“衍生品”的定义就是一种“金融合约”,即“合同”。从“金融合约”到“金融商品”的转化,体现了衍生交易与传统商事交易的相异之处,但它依然是在合同的一整套逻辑之下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以合同为研究对象的法律人比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或者公众更有优势来获得对衍生交易的清晰认识。可以说,从“合同”入手来观察衍生交易,有助于我们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把握衍生交易的本质与逻辑,将看似错综复杂的衍生交易法律问题条分缕析、梳理清楚。本文的目的即以“合同”为中心,还原衍生交易市场规则背后的法律逻辑,最终提出关于金融衍生交易法律问题的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11]

上一篇:摩根大通:韩国金融股下跌现买入良机,看好银行股回报提升
下一篇:A股重要指数,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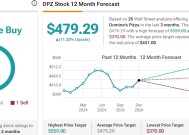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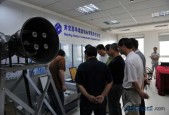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