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锦添:我试图用一种虚拟的方法来接近《红楼梦》的美
- 体育资讯
- 2024-12-23 15:04:59
- 24
【编者按】
叶锦添,曾担任电影《卧虎藏龙》《无极》《夜宴》《赤壁》《风声》《一九四二》和电视剧《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红楼梦》等的美术指导,并凭借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和英国电影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在他担纲美术设计的这些著名影视剧中,《红楼梦》是备受争议的一部,很多人都觉得无法接受剧中的人物造型,而对此,叶锦添本人是有着自己成熟的思考和美学主张的。将现实和虚幻交织,在复古的同时也加入非常多的现代元素,从而完成一种似有似无的时空模糊感。
本文摘自《叶锦添的创意美学:流形》,由澎湃新闻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叶锦添
汤显祖写《牡丹亭》,描述少女思春的情怀,使中国的庭院幻化成青涩欲望的花园,那只是幼小而不成熟的灵魂,却令人魂牵梦萦。中国的人情总是借景喻物,看到庭院里的廊,有着不同形状的窗户,每个窗户都直视着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番景象。那妙在陈设,流离于形式之间,产生一种暧昧的情愫。如大型昆剧《长生殿》的神思陌路,在《红楼梦》里面提到各种花草树木,各有各的属性,十二金钗也用了不同的花来形容她们的本质、她们行事的风格。古典戏曲的剧照,从男扮女的各种神态,都有一种特别的妩媚,因为这种错置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中国文化——一种很情色的东西,不是色情文化的情色,而是暧昧,里面藏了很多诗意。我看《红楼梦》,感觉到曹雪芹身上也有这样一种象征主义的氛围。他把十二钗形容得很美,每个人都有不同,但各自都是悲剧收场。叶锦添凭借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
《红楼梦》的开始,也是以神话开篇。一块石头与一棵仙草在女娲补天的时候被遗弃了下来,成为无用的存在。石头以天上的水滋养了仙草千万年,那仙草就是林黛玉,她无以为报,只能以眼泪相送,开启了石头记的故事。他们为了感受人间的经历,一起约定到达人间,经历这一辈子的人间故事。到了人间,他们经历了一个颓废荒唐而又凄婉空灵的青春梦魇。一种灰蓝的色调,却装点着华丽的色彩,深藏在曹雪芹脑海里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收拾往事的梦。然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我感受到的《红楼梦》总是充满哀伤,不止是那种不完整性,《红楼梦》牵引着中国人情绪的依托。曹雪芹营造的美,是逝去的美,有很重的象征色彩,这样东西无法用传统符号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争取一种我所期待的空间,色彩是《红楼梦》能给我的强烈印象。曹雪芹收藏的风筝,丰富色彩早已深入民心,《红楼梦》虚实并置,看着孙温的画本,林黛玉婉弱雅幻之姿,又浮现精细及带着浓烈的神秘感与伤逝色彩。电视剧《红楼梦》定妆照
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有古典也有现代的两部分,但是要把它统一起来,而且对人物有进一步的印象,尤其是十二金钗经常同时出现,又符合统一的调性与特别的性格。这次采用了国画原色调的发展,但把主要的色调调成了现代的,因为要呈现年轻人的气场,尝试把美术上的表达模式装置在中国的意境里,使之产生虚拟的美感。中国造型的美学来自诗,它可以转化成形式,可以转化成故事的调度,演员的走位与做态,创造一种新的戏剧语言的表达方法。不管是舞台的运动还是布景的处理,最后都是要在现实空间里面去做改造,建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使既有的形式产生活泼多样的变化,达成虚拟诠释的美感。
小说里有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如果完全写实可能会失去一些灵气,它是一个梦境,梦里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和想象的东西。曹雪芹并不那么写实,他的小说是一部很强烈的失乐园,总是带着一种自嘲。他写十二金钗,寄托了他对美、对童真的向往。其实到他老的时候,他内心还是个小孩子,作品里寄托了他的孤独和对纯真的向往。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款人物造型
想象《红楼梦》的语境是完全的中国语境,为了摆脱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一直想找到能代表这种语境的东西,这种虚拟和真实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表现方式。《红楼梦》本身把朝代模糊掉了,我试图用一种虚拟的方法来接近那种美,照顾到世界的审美眼光。书里明确点到的服饰,我们必须在创作里做一个选择:就用比较艺术的方法来处理而不是还原。直接走入曹雪芹的世界,他虚的地方虚,他实的地方实。在很多中国戏曲的资料中,1912 年上海的京剧演出盛极一时,他们对京剧舞台进行了革新,用到了许多西方舞台的效果,如布景和假山石。我看梅兰芳演出的照片,艺术性很强,他对服装、布景的更新很迷人。我在其中找到了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这种风格是什么呢?就是实景和布景的诗意结合。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走廊,后面是大观园的布景,远处是天边,天边还有暗光。房屋比例也不是完全正常的比例,一半是搭的,一半是真的,是写实的底子,但也非常舞台。我们拍每个镜头,前面都可以再摆个东西,或者有人走过。我们永远都在几个层次里拍戏,我认为这是半写实主义。王熙凤(姚笛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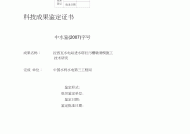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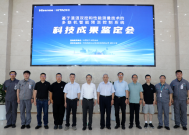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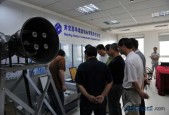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