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移民美国到中国越南妈妈,何以为家? | 社会观察
- 体育赛事
- 2024-12-23 04:01:50
- 18
原创 深度营 深度训练营
从记事起,广东云浮人陈向就常听妈妈说起家乡的故事。那里有硕大的榴莲,芳香的茶叶,家里种了许多菠萝蜜。故事的结尾,妈妈总会叹口气说,“回不去了”。
陈向的妈妈是越南人,年幼时得过脑膜炎,看起来有些“呆傻”。1993年的寒冬,她被越南同乡拐骗到广东云浮,和一个残疾的男人结了婚,生儿育女。
类似的事件在上世纪末也曾发生过。除了经过移民程序和婚姻登记的合法跨国婚姻外,许多越南女性因婚姻买卖或边境通婚进入中国,与中国男性结婚生子,就此定居下来。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南新娘。目前尚不明确国内越南新娘的具体数量,据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李代荣、伏智飞《关于越南新娘问题的再研究》一文,最近的数据停留在2016年,中国约有6.5万名越南新娘,这一群体最先出现在广西、云南等中越边境地区,而后分散到广东、福建、浙江。
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兼任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理事的薛瑛指出,这种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弱弱组合”。越南女性往往流向经济能力弱的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与身份缺失也让她们成为不被看见的人群。薛瑛长期关注社会性别与国际问题,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开始关注越南新娘群体,发表有论文《中国“越南新娘”的权力视角分析》。
对于这群长期滞留他乡的越南女性来说,故乡与现实之间早已不只是一条河流的距离,“家”的含义也变得模糊。一位受访者曾问自己来自越南的妈妈为何不回家,得到的回答是,“已经有了孩子,就不回去了,落地生根吧”。这些从小听着越南的故事、见着母亲眼泪的孩子,感知到了母亲的特殊命运,长大后,她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为母寻亲的道路。
越南芒街与广西东兴隔岸相望,很多越南人选择从这里来华——过了河就是中国。那是1994年,越南人阿莲和同乡的女人赶了一天路,抵达边境。同乡告诉阿莲,中国的缝纫机便宜,她们相约一起过境买回来做生意。
阿莲错信了同乡人。她们乘船过河,到中国时,天已经黑透了。女人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带她上了一辆出租车,阿莲被丢在女人的中国同伙那里。
三天后,一个名叫阿青的男人用几千块钱买下阿莲。阿青是广东化州人,生活贫困,一直没能成家。买下阿莲的时候,阿莲三十出头,而阿青已经五十多岁了。
一开始,阿莲每天都想逃跑。找不到离开的方向,阿莲就在山里躲起来。这时候,阿青一家人会上山寻找,跑不掉的阿莲便留了下来。
刚来的时候,阿莲不懂中国话,更不认识字,只能用手比划着和阿青交流。如今她已经学会讲化州方言,也听得懂普通话。长久地相处过后,阿莲渐渐发现眼前的男人还算忠厚可靠,为他生下了一儿两女。
这是曾青莲父母的故事,爸爸叫阿青,妈妈叫阿莲,便为她起名青莲,她是家里的大女儿。从六、七岁的时候,曾青莲意识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有所不同。他们的父母没有这样大的年龄差异,家里也没有一下雨就漏水的瓦房,生活条件比自己好得多。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少了什么,妈妈给了她足够的爱,“就算生活条件差也能苦中作乐”。
2021年9月,晚饭后,阿莲在洗碗
(图源受访者)
张甜的成长故事与曾青莲的有着相似设定:母亲是被拐来的越南女人,父亲是中国男人,父母年龄差距很大,从小家庭贫困。
华东政法大学邱格屏教授在《被拐来的“越南新娘”——犯罪学的分析》一文指出,这些“嫁”来的越南姑娘在与中国紧邻的越南贫困乡村里长大,自小就听说中国的生活很好,到中国能赚大钱。
邱格屏研究发现,在其整理的117份拐卖越南女性的判决书中,涉及222名“越南新娘”。其中82%的“越南新娘”主观上具有流出意愿,42.3%是想来中国工作。这种主观流出意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库存知识的有限性造成的认知偏颇,最后被利用骗到中国,进入中国后被进一步转卖。
张甜的妈妈叫阿六,年轻时想来中国赚些钱,却被同行的朋友欺骗,藏在火车的尾箱里,辗转多趟火车,九天九夜后到了潮州。
2000年,阿六被丢在一对潮州夫妇家里,那里还有十几个同样被拐来的女人。在被卖出去之前,她们是这对夫妇的“仆人”,任由使唤,不听话就会遭到打骂。阿六曾用没拧干水的抹布擦地,被夫妇看到后,拿着皮带抽打了一顿。“她反抗不了,只能挨打”,张甜说。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男人来这里挑选,这时候,女人们要站成一排供对方选择,男人付完钱就可以直接领走。一个43岁的男人用8000多元买下阿六,回家后办了场酒席,算是“结成婚”。
结婚次年,阿六生下张甜,两年后又有了弟弟。在张甜模糊的记忆里,父母相处得还算不错,爸爸从未打骂妈妈,家里人也“对妈妈很好”,教妈妈说中文和潮汕话,给妈妈买新衣服。
但并非所有越南新娘都能被平等对待。在某些情况下,越南新娘的婚姻像一场筹码不在自己手里的赌博。被拐后,她们的命运走向几乎尽数取决于男方。买卖婚姻中,男方的质量良莠不齐,越南新娘们不一定能遇良人。张甜记得,村子里有很多被买来的越南新娘,不时有人逃走。在这些家庭里,男方大多经常打骂女方,张甜曾看见爱赌钱和喝酒的邻居男人将自己的越南妻子踢下楼梯,而后在公路上对妻子大打出手。
薛瑛指出,“男方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身上多有懒惰、赌博、酗酒等家庭恶习,要么大概率是残疾。”由于语言不通,缺少生存能力,没有合法身份,大多越南新娘的反抗方式是偷偷逃跑,“要么认命,要么逃离,除此之外没有合法的自救方式。”
拐卖越南女性事件为何出现?邱格屏认为,这背后是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市场造成挤压,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农村出现大量的男性“婚姻剩余人口”。邱格屏进一步强调,贫穷是导致收买人收买越南女性为妻的重要原因,收买人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不能正常迎娶妻子。
在“越南新娘”的生意链条上,一端拴着认知有限的越南女性,另一端拴着娶妻心切但条件不佳的中国农村男性。这个链条将越南新娘送到陌生的地方,生下孩子,成为妈妈。
阿六如今的房间只有几平米,有些偏仄,放进一张床后,只留下一条狭小的过道。因为“不太会讲话”,她很少与人来往,也不出远门,闲暇时间摆弄下花草,种些蔬菜。
张甜和妈妈在潮州的家
(图源受访者)
张甜六岁的时候,爸爸因病离世,妈妈阿六开始支撑这个家。因为是“黑户”,又没什么技能,生活有些艰难。“没办法去上班,没有身份证别人不肯收,被查到要罚钱的。”
可以说,合法身份的缺失是越南新娘面临的困境之一。薛瑛表示,虽然越南新娘生活在中国境内,却是“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的“三非人员”。法律身份缺失之后,工作、生活、社会保障,都是难题。
最显而易见的是贫穷。一开始,张甜一家靠捡福寿螺赚钱。这种螺壳薄肉多,既可食用,又可做高蛋白饲料。母女俩常常一大一小伏在田里,忙碌大半天能捡二三十斤,回收价四五十块钱。后来,经亲戚介绍,阿六又去给祭拜用的纸钱刷红漆。
张甜和弟弟再长大一些时,阿六去了玩具厂做女工。工厂是私人作坊,不需要身份,员工也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妇。有时候,阿六负责给玩具装箱,按小时计费,一个小时七八块钱。有时是做手工,按数量计费,阿六手脚比较慢,一天下来只能赚二十多块钱。
“小时候家里很苦。”张甜说,妈妈微薄的工资负担不起家庭开支,一家人常在傍晚去菜市场捡摊主不要的菜。没钱买衣服,张甜和弟弟就穿亲戚不要的旧衣服。家里没通热水,她们就捡树枝运回家烧水。在张甜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她常骑着装满树枝的小车,颠簸在乡村的土路上,妈妈跟在后面为她推车。
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张甜就帮着妈妈一起补贴家用,弟弟也从中学开始在火锅店里做兼职。
紧随合法身份缺失而来的是社会环境的不认同。中央民族大学鱼耀在《生存有道:中越跨境婚姻中的嫁与家》一文中指出,公民身份缺失造成制度性歧视,限制了越南新娘关系网的扩展渠道,村庄生活存在的隐形歧视则影响了她们的交往深度。双重因素影响下,她们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种“客居”状态。
因为是黑户,阿六无法参加医保,去不了大医院看病。疫情期间,阿六无法按照正常流程接种疫苗,进不了超市和商场。工厂的人嫌弃她,让她干活时不要坐太近。张甜记得,那时候妈妈常一个人在角落里工作。
越南新娘的孩子也可能被霸凌。爸爸离世,妈妈又不被人“当回事”,张甜回忆,自己和弟弟上学时常被人欺负,自行车被踩坏、车胎被扎、帽子被丢在要喂猪的剩饭桶里……张甜有个要好的朋友,也是越南妈妈的孩子,也常常被欺负。
阿六常告诉张甜,“家里没有顶梁柱,咱们母女俩就只能把苦往肚子里咽”。
提起妈妈阿莲,曾青莲一度哽咽。家里贫困,爸爸年纪又大,“农活基本是妈妈一个人做”。妈妈种菜、养鸡,用微薄的利润填补开销,每天四五点起床做饭、打理家务,之后就一头扎进田里,一个人可以收拾完四五亩田,干完自家活,又会去别家帮忙。
在她眼里,妈妈勤奋友善,常常给别人帮忙。有次过节,亲戚朋友来家里聚餐,一位老大爷不请自来,在家门口拉二胡,以此索要钱财。其他人大多都比较抗拒,阿莲却给了钱,还邀请他上桌吃饭。
薛瑛进一步指出,越南新娘嫁到中国后,往往面临族群、阶级和性别上的歧视。因此,她们生儿育女、勤俭持家、照顾邻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周围环境的认可。
总的来说,越南新娘更倾向与其他有相似遭遇的越南新娘建立关系。上述论文里,鱼耀提到,越南新娘们通过彼此互动,一方面弥补关系断裂带来的心灵空缺,一方面间接地认识她们在中国一侧的家人,拓宽其相对狭窄的人际网络。
阿莲便交了些关系不错的越南朋友。
越南女人爱戴一种圆锥形的帽子,有一次上街买鱼,阿莲看到有女人戴了这种帽子,还随口说了句越南话,便认出对方是越南人,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
“在中国的越南人会有自己的圈子。”认识了一两个越南女人后,阿莲通过她们结识了其他越南人——大多都是被拐来嫁人的。这些越南朋友偶尔会来阿莲家里聚着,用家乡话聊天。
2021年10月,阿莲、曾青莲和青莲孩子的合照
(图源受访者)
离别几十年的“河对岸的家乡”,是被拐来的越南妈妈内心共同的隐秘角落。
张甜常听妈妈阿六提起越南。那里遍野是山,有芒果、榴莲和玉米,妈妈在家排行老六,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她总会看到妈妈流着泪,刷一些有关越南的视频。
而阿莲,她从越南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台收音机,里面都是越南歌曲,她一闲下来就会听。过节时,化州当地会表演越南的戏剧,这让她想起年轻时在越南的时光。
她们的女儿,张甜、曾青莲和陈向,从小便听着越南的故事,见着母亲的眼泪。长大后,过去的种种将她们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妈妈回家。
纪录片《阿紫》剧照
陈向今年29岁,云浮罗定人。她接触过许多和妈妈一样的越南新娘,这在她的家乡很普遍,“挺多的”。有的十几岁就被卖过来,有的和妈妈一样有些“呆傻”,她们大多对自己的家庭信息印象模糊,“如果没有人帮他们寻亲,可能这辈子都望乡路远”。
2019年,工作步入正轨后,陈向便开始着手为妈妈寻亲。为了能多一些寻亲的线索,她报名网课学习越南语。那段时间,她每天读一篇越南语文章,听二十分钟越南语音频,孩子出生后也没中断。“帮助妈妈回家一直是我的心病。”她还专门在网上结交越南的朋友,“一方面提高口语水平,另一方面想看看有没有帮妈妈回家的线索”。
转机发生在2020年6月,陈向结识了丈夫厂里的一位来自越南海防的阿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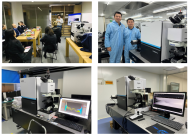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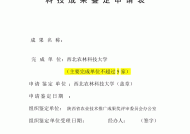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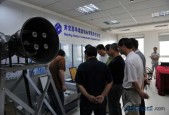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