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高级英语下册课文翻译
- 欧洲杯直播
- 2024-12-16 07:24:50
- 22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英语专业(本科段)
高级英语(下)
王家湘
课文翻译
Lesson One
The Company in Which I Work
我工作的公司
约瑟夫·海勒
我工作的公司里,每个人都至少害怕一个人。
职位越低,所惧怕的人越多。
所有的人都害怕那十二位顶层上司,他们帮助创建了这个公司,而且现在仍然大权在握。
所有这十二位都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岁月的沧桑和对成功的执著追求使他们心力交瘁。
他们中很多人在这儿干了一辈子。
当我在大厅里遇见他们时,他们看上去非常友善、沉稳而心满意足,而且他们与别人一起乘坐公共电梯时又总是彬彬有礼、沉默不语。
他们不再努力工作。
他们主持会议,决定别人的晋升,任凭别人在准备发布的通告中使用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谁真正经营这家公司(甚至连人们认为现在经营着这家公司的那些人都不知道),然而公司的确在运转。
在平常的工作日里,我很害怕杰克·格林,这是因为我所在的部门属于他的部门,而杰克·格林是我的上司。
格林害怕我则是因为我的部门的绝大部分工作是为销售部所做的,而销售部比他的部门更重要,而且同他相比,我与迪·卡葛勒以及销售部的其他人员的关系更加密切。
格林偶尔也对我不信任,他有时会向我表示他希望我的部门的每一项工作在其他部门知道前要先让他知道。
我知道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自己的工作非常忙,根本就无暇顾及我们所有的工作。
我会将大部分工作绕过格林并直接交给需要它们的人,而不愿意占他的时间。
毕竟我们部门绝大部分工作只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每当其他部门赞扬我们部门的工作时,格林就会变得不安,如果他从未看见或听到过的话,就更是恼羞成怒。
在我的部门里,有六个人害怕我,其中一个小秘书害怕我们所有的人。
有一个为我工作的人,他对任何人都毫不惧怕,甚至连我也不怕,我真想尽快把他解雇掉,然而我害怕他……公司里非常惧怕大多数人的人是销售人员,他们都生活和工作在极大压力之下,当情况不好时,对销售人员来说就会更糟。
而当情况较好时,他们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不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个人,他们总是在接受检查,总是处于不合格的边缘。
他们工作非常努力(就连他们中那些很有保障的和充满自信的人都是这样)以使在书面评语上看上去好一些,况且要让他们看上去好的表格多得很。
比如每星期为各部门准备的每个销售办事处及销售部所作的前一星期的销售业绩总记录加以保存并且与前一年同期的销售业绩相比较。
这些数字被复印后发到公司的每位员工和与销售有关的部门。
这样做的结果是公司几乎一直在对每一个分公司的销售办事处中的销售人员在某一既定时间内的工作业绩进行公开审查和评论。
当销售人员业绩好时,他们因为要开始使工作做得更好,以免不如以前,从而感到压力
重重。
当他们的业绩不佳时,他们就会做得一塌糊涂。
当一个销售人员争取到了一份大订单或者得到了一笔大的应收的账款,他的兴奋也是短暂的,因为很可能他的那份大订单或者大笔的进账下一次有被竞争对手的公司拿去的危险,甚至在完成前被取消,对这种情况没有人能肯定谁输谁赢。
因此即便在他们的喜悦中也存在着危机和惊慌。
然而,销售人员热爱他们的工作,而绝不再选择其他职业。
在没有消化不良的困扰或不再苦苦为未来忧虑时,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爱说爱笑的人。
另一方面他们会突然之间变得任性并且牢骚满腹,他们每个人都至少能说出公司的一个上层人物是令他极度不满并且觉得这个人会毁了他的前程的。
销售人员工作努力,薪金丰厚,还有个人经费,他们会把这笔个人经费挥霍在进出公司的其他人的身上,其中包括我本人。
他们在豪宅区拥有自己的房子,在高级的私人高尔夫球场打球。
公司鼓励这种做法。
实际上,公司为他们支付乡村俱乐部会员费以及他们在那里的所有开支,并且对那些在高尔夫球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销售人员给予奖励。
销售部不要未婚男士,甚至连丧偶的也不要,因为公司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对未婚销售人员来说与前程似锦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他们的太太们进行社交来往或者参与重大的活动不仅很困难而且危险。
如果一位销售人员的妻子去世了,而他又没有准备再婚,那么通常在丧期后的几个月内他就会调去做行政管理工作。
单身汉永远都不会做销售员。
离婚或者丧偶的销售员都很清楚他们最好再婚或者去另谋他职。
非常奇怪的是,销售人员对长期压力和他们所受的严格管理能够坦然处之。
他们受到纪律和上级指令的激励和促动。
他们在上司的点拨下获得成功,业绩蒸蒸日上。
当他们不是烦躁焦虑或者沮丧时,大多开朗、充满自信而且很合群。
一个人一定是具备某种特殊的性格和气质才使他不但从事销售工作而且想做一名销售人员。
销售员们不仅对他们的岗位而且对他们在公司中享有的地位及重要性感到自豪。
因此我的部门以及其他的大多数部门的职能就是协助销售人员的推销,公司就是靠销售生存。
这就是我们受雇佣拿薪水的原因。
公司里最不担惊受怕的人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市场调研部工作的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他们从不担心任何事情,而只关心对公众、市场、国内以及世界的统计信息的收集、组织、解释以及重新组织。
但有一点,他们的工资很少,而且他们也知道如果一旦失去这里的工作,这么少的工资,在其他公司找份工作并不困难。
他们的预算也很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允许承担过大项目。
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从贸易协会和一些政府机构免费得到的,而且对于我们所发布的信息的来源真实与否也无从知晓。
然而这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出自一个信誉好的来源。
市场调研部的人们从没有因为他们在公司外发现我们处于竞争劣势而受到责备。
他们不能改变现实,而如果他们能的话,也只能发现它并提供巧妙的方法来掩盖它。
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工作的性质。
而且所有格林的属下与销售部和公共部密切合作,
从而将全部的事实变成一半,而把一半事实变成全部。
虽然我不是总能欺骗我自己,但是却很擅长这些骗人的把戏。
实际上,我经常为公司的人们被自己的宣传所欺骗而吃惊,现在有很多人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销售人员是这样,那些精明能干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这样。
和我同级的人是这样,比我低的人也是这样。
就连公司里几乎所有从高级商务学校以优秀成绩毕业的人们也不例外。
比如,每当我们举行一个新的广告活动,公司内部的人总是最先被蒙骗的,每当我们介绍一种新的产品,或者换了外包装、颜色并起了新的品名的老产品,即使一点也不好,公司内部的人总是第一个赶着去买的。
我想,知道自己愚蠢的人是聪明的,而知道自己撒谎的人是诚实的。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自作聪明。
我们这些在公司这儿的聪明的成年人,整天悄悄地出没于办公室,大家互相惧怕并试图躲避令人生畏的人。
我们上班,吃午饭,回家。
我们迈着正规的步子进进出出,下班后和其他部门的伙伴一起外出,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才回家。
实际上我时常问自己,仅取决于办公室情形的好坏,或者是家中我妻子、弱智的儿子、另一个儿子、我的女儿、黑人保姆以及照顾我的弱智儿子的护士情况的好坏,他们的情形如何,这就是我要做的全部吗?难道这真的是我有生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多的吗?
我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永远是——是的!
我现在经常对工作非常厌烦,每项常规的工作我总是交给其他人处理,而这使我更加感到厌烦。
要判断究竟是干令人生厌的工作更加烦人,还是将令人生厌的工作交给他人处理,然后无所事事更烦人,这真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当任务又大又紧而且有些令人生畏还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时,我就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我变得惴惴不安,而且夜不能寐。
但在这种极有刺激的压力下,我的表现最佳,也最喜欢我的工作。
我独自处理所有这些重大的项目,并且当我成功地完成时,我会因受到赞扬而沉浸在极大的自豪与虚荣之中。
但在这些挑战与兴奋的巅峰之间是单调与绝望。
(而且我也发现一旦我给某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不再为给同一个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感到兴奋不已。
在度过每次危机后,都会有一次大的情感失落,一种空虚和令人悲哀的失望。
去年的威胁、机遇和鼓励经常会成为今年不可避免的冗长乏味。
我常常觉得我被利用了,这只是因为我被要求做给我报酬的工作。
)
在我极度悲伤的日子里,我便开始将公司的人员结构列入图表……根据嫉妒、希望、恐惧、雄心、烦恼、对手、痛恨或失望,将公司的人员分类。
我把这些表格叫做我的“快乐图”。
这些恶作剧总是使我精神振奋,然而都非常短暂。
这样分析公司时,我的排名非常靠前,因为我既不嫉妒也不灰心,而且我胸无大志。
排在前几名的当然是这些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年轻又没有靠山的人。
对他们自己来说,公司还不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机构,而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并且认为他们目前的状况只是短暂的。
我之所以把这些人排在首位,是因为只要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后半生是否为公司工作,不管有什么样的诱惑,他都会响亮地回答
“不!”我也曾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给你一个响亮的回答:“不!”并且还要补充上:
“我想我宁可现在就死!”
然而我没有任何离开的打算。
我现在有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没有任何地方是我的容身之处。
Lesson 2
Eveline
伊芙林
詹姆斯·乔伊斯
她坐在窗前看着黄昏涌上大街。
她的头靠在窗帘上,鼻孔里满是提花窗帘布上的尘土气味。
她累了。
很少有人走过。
最后一所房子里的那个男人经过这里往家走;她听见他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走过水泥道,然后又嘎吱嘎吱地踩在新红房子前的煤渣小路上。
过去那里曾经有一块空地,他们每晚都在空地上和其他家的孩子一起玩耍。
后来一个贝尔法斯特来的男人买走了那块地并在那里建了房子——与他们棕色的小房子不同,他的房子是明亮的砖房还有闪亮的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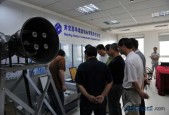







有话要说...